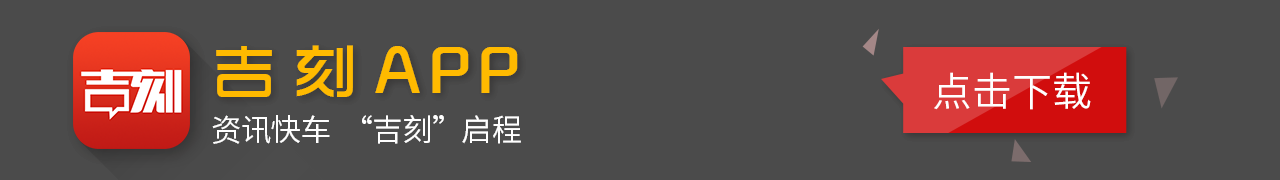电影与文学要相互成全
在经历了一段欲说还休的改档风波之后,原本就自带话题的冯小刚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终于在11月这个传统“冷档期”火热上映。虽然都由刘震云亲自操刀改编,但《我不是潘金莲》与《一句顶一万句》之间的水准分野,不仅验证了资深导演与菜鸟导演在生活经验、艺术判断力和创造力上的巨大差距,也充分证明了电影作为一种二次创造艺术的再造空间,以及它与文学艺术之间相互成全的可能性。
《我不是潘金莲》出版于2012年,是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长篇新作,其创作灵感据说与其作为底层妇女维权律师的妻子有较大关系。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20年间不断上访的故事。农妇李雪莲为了生二胎,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没想到离婚后前夫竟然另觅新欢结了婚,倍觉屈辱的李雪莲起诉前夫败诉,从此层层上访,屡屡受挫,越挫越勇,欲将法官、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等全部告倒。一路到了北京后,阴差阳错在某省人代会驻地遇上中央首长并向其陈情,其后从市长到县长统统被罢官,然而李雪莲想要洗刷的“我不是潘金莲”的“冤情”并未解决,仍然年年上访。20年后,新一届全国人大即将召开,从县到市的各级领导使出浑身解数,要阻止李雪莲再次上访,几番波折后,事情竟然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得以终结。
与《一句顶一万句》釜底抽薪、伤筋动骨的改编不同,电影版《我不是潘金莲》除了将时间间隔由20年改为10年,压缩调整了个别人物和细节,在内容层面基本完整延续了原著,真正的大改动来自于导演将文字电影化的二次创造,它为一部原本生活流的看似更适合纪实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赋予了一种抽离于现实,更具形式感和风格化,富于韵味和寓意的实验性的美学形式。
圆形画幅的中国古典意趣
早在今年3月放出的《我不是潘金莲》预告片中,冯小刚就已经用让人惊艳的圆形画幅制造了不小的轰动,而成片最终揭晓,片中除了圆形还有正方形,倘若再加上宽银幕画幅,全片实有三种画幅。采用这种反常规的实验性画幅,除了可能招致的形式主义批评,主要的顾虑包括画面信息量减少、观众的视觉适应性以及相应的商业风险等,而冯小刚最终力排众议进行影像实验,其根本原因应是自我挑战和美学创新的激励。
事实上,与美学形式主义者张艺谋不同,冯小刚此前在电影里几乎从来没有表现过明显的对于形式美学的探索意图,《甲方乙方》、《大腕》等喜剧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话剧化的,向来以机智幽默的台词而非精心打磨的影像著称;而《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以及《一九四二》等现实主义作品则追求自然写实风格;即使是《夜宴》,更为突出的还是在服化道上的用力。虽是美工师出身,冯小刚此前似乎对于镜头语言的形式美学并不感冒,然而当其决定来一次美学实验时,却比此前的探索者都更加激烈。事实上对于银幕画幅的实验,近几年贾樟柯、侯孝贤都在玩,但都没有如冯小刚这样极致。
圆形画幅并不是中国画的专利,欧洲古典绘画中拉斐尔、安格尔等大师都有圆形画幅作品,然而《我不是潘金莲》中呈现的圆形画幅则的确有着中国古典美学的典型风格。宋元兴盛的纨扇绘画以人物、花鸟为主,兼有少量山水,即使人物画,往往也与花鸟和山水相融,虽以工笔为主,但仍是清淡写意的线描,与西方圆形画幅人物油画中满满的肉欲截然不同。该片圆形画框中的江南烟雨、蓑衣竹筏、水乡民居,当人物被嵌入其中时,便有了典型的中国古典意趣。
采用圆形画幅同时意味着镜头景别、角度、运动、构图以及相应的布光方式的变化。强调感官视觉刺激的特写镜头几乎消失,主演范冰冰在全片中无一特写,中全景成为影片的绝对主体,创造出与古典绘画相似的远观视角。即使片中明显模仿安格尔名作《大宫女》的范冰冰裸背镜头,同样将巨大的窗框及外景作为画面的主体。在构图上,传统的九宫格三分法也被打破,对称构图、水平分割等被更多使用。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奇观化综合运动长镜头,也被片中的静观所取代,即使运动,也是相对舒缓的水平横移。这种与对象保持审美距离的凝视姿态,正是典型的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现。
方圆画幅的政治隐喻
片中的方圆画幅各有其寓意。圆形画幅只出现在地方/民间,当故事发生于北京时则转换成方形画幅。尽管“天圆地方”的解释过于抽象而缺乏说服力,但当“方形”的严谨规整与中央、政治、权威的寓意相对应时,似乎便有了成立的依据。为了让观众适应画幅变化,影片对于画幅的引入和转换设计颇为用心。开场口述潘金莲故事时,使用今人画家的仿古圆画幅插画,从而自然完成圆形画幅的引入,而在画幅转换时,通过出圆形隧道口而转方,又通过圆形窗框构图而回圆。方与圆在画面内的并置也颇有寓意。当麻烦无意中解决,市长马文彬与县长郑重在谈话时,景深中方圆并存的灯饰,正与对话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体、官与民的关系形成呼应与隐喻。
尽管关于画幅的实验事前曾颇令人担忧,但事实上圆形画幅并没有影响观众的观看,兴趣点能够始终聚焦于画面本身,而它所创造的古典化审美风格,以及与作品主题相对应的象征寓意,则使其避免了为形式而形式的陷阱,为这个高度中国化的故事,寻找了一种中国化的美学形式,应该说这个实验还是成功的。
白描式呈现中国生态
除了形式实验,《我不是潘金莲》的另一个突破在于其题材。虽然看似与《秋菊打官司》相似,但该片并不是一个普法故事,而是一部黑色幽默的讽喻式电影,借助一个农妇的上访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对官场生态、官民关系进行观察和反思。虽然官场小说历来是畅销书榜上的热门,但新中国成立后此类影片可谓屈指可数。吕班导演的讽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是开先河者,影片用漫画式的方式嘲讽了欺上瞒下、马屁逢迎的官场陋习,然而随着时代气氛的变化,讽刺喜剧很快被歌颂喜剧和生活喜剧所取代。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建新在《黑炮事件》(1986)、《错位》(1986)、《背靠背,脸对脸》(1994)等片中,对文山会海、官僚主义、权力对人的侵蚀和异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表现。有意思的是,在该片中黄建新客串了省长一角,奉献了颇为准确传神的表演。
将《我不是潘金莲》置于电影史背景去考察,便不难发现仅就题材选择而言,它已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事实上,由于题材相对敏感,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已尽量弱化故事本身的刺激性。农妇李雪莲的遭遇在道德上值得同情,然而其诉求在法律上却并不成立。至少在李雪莲事件上,各级官员并无腐败受贿,甚至他们的被罢免也多少显得无辜。片中官员们被李雪莲玩得团团转,狼狈不堪。片尾市长马文彬对于干群关系的反思,显然也与主导价值所倡导的政治正确相一致,这种“建言献策”、“解决问题”的角度,对于降低影片可能的风险显然是有利的。
对于这部讽喻式电影来说,李雪莲未必是真正的主角,她不过是一个串场角色,借助其呈现与之相关联的社会世象,尤其是政治生态、官场生态,官与民的关系,国家与个体的关系。相对于吕班与黄建新的影片,该片的方式是白描,以及寓言化的隐喻。通过故事发生地光明县,以及法官王公道、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沪浜、省长储清廉这些地名人名的隐喻,反思官与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访与截访,反思政治与法律、行政与司法的关系。通过核心事件的源起,思考集体意志、群体价值与个体诉求、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通过李雪莲事件看似荒诞的发展过程,白描式地呈现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和运行机制,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级领导与人大代表之间的关系等等,其间蕴含的细微的社会与政治意味,或许只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的观众能够理解。
即使对于个体而言,影片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作为个体的李雪莲,既复杂,又简单,既引人同情,也令人无奈,既心理脆弱,又大胆敢为,既果断坚持,又固执甚至偏执,既缺乏法律和制度常识,又有其智慧和狡黠。片尾画外音淡淡说道,多年后,李雪莲已经渐渐忘记了这些往事,她甚至会跟别人一起聊起来,似乎讲的是别人的故事。这当中包含的对于体制、文化乃至国民性的悲情和反思,着实耐人寻味。
从喜剧高手走向艺术家
或许只有从讽喻的角度,能够理解该片在形式实验上的选择。正因为它是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寓言化的故事,所以才为某种抽离于现实的、隐喻式的形式表达提供了可能。除了圆与方,片尾终于回归了常态的长方形宽银幕。李雪莲在北京火车站外开了一个连骨肉汤小店,竟然巧遇了当年被罢官的史县长,谈起当年的往事,两人不胜唏嘘。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明亮结局,冲淡了前一场景中范伟饰演的守园人所展现出来的残酷的人性真实,然而,这一段落使用的强烈的柔光效果却有意暴露了梦幻般的不真实感,或许也验证了其作为补拍段落的传言。
可以预言该片会引发的争议,激进的批判者或许会觉得该片过于温和,甚至美化了现实,而秩序的维护者或会觉得影片有丑化或攻击的嫌疑,这也正是创作者和监管者对此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原因。这种截然对立的两极化反应,本身就是当下中国复杂多元、矛盾冲突的思想状况的真实反映。
在凭借喜剧电影获得巨大商业成功和市场声誉,乃至成为春晚导演之后,冯小刚终于可以拍摄顺心而非顺势的影片,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再到现在的《我不是潘金莲》,他离此前那个没心没肺的商业喜剧高手形象越来越远,离一个忧生伤世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艺术家形象越来越近,凭借已获得的经济、文化、体制与人脉资源,对于如何在内容禁区与表达自由之间寻找话语缝隙的技巧也更加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