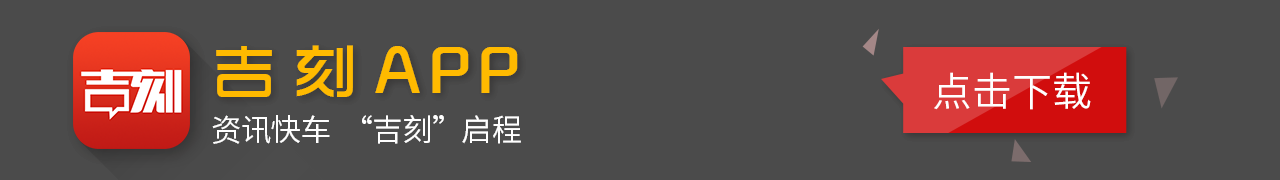作家金宇澄(网络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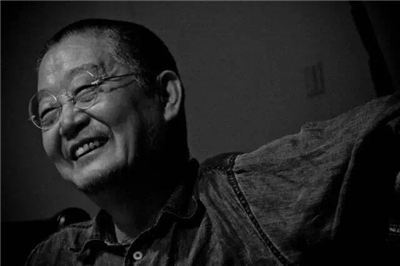
作家阿城(网络截图)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旧影纷繁,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直至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那些细节。这部分的内容,经金宇澄整理成独立的一章,加上作者记取父辈的非虚构长文,书名《回望》。
如金宇澄所说:“花朵犹如人生细节,它有枯萎和干瘪的过程,如果你疏忽它的特殊性,它们将消失,而冷静的历史,仅是巨兽沉重的骨架,或许是无法失落的遗迹。对于历史学者,粗线条的骨骼组合是重要课题,细节是轻烟与飞尘,也是流星,它难以捕捉。”
上周六,很少出席公众活动的作家阿城也破天荒地首次为一本新书站台,和金宇澄及读者谈《回望》谈《繁花》及其他。
非虚构·小细节
问题:《回望》是非虚构写作,里面写到您父亲当时从事地下工作,有大量的细节,有的故事甚至很惊悚很传奇,有没有虚构的成分?
金宇澄:我特别喜欢中国式的叙事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叙事很大规模地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我很喜欢一些简单的笔记类的东西,比如李伯元的《南亭笔记》,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但写作非常简洁。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不是里里外外掏出来,就是几句话,一些碎片化、生动的人露出来,这种阅读和用砖头一样厚的书来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有另外的感觉。
写到《回望》的时候,我父亲做地下工作,它根本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谍战片一样,像钟表一样算计的很准,里面有大量人为的失误。这些偶然性的失误,是不会被历史记录写出来的,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不太爱看头头是道,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我特别喜欢看一些类似于八卦、细节的文章。所以我在《回望》里有时会触及到一些小细节,或者说,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
所谓非虚构的写法,有一种是非常仔细地梳理一个一个人物,甚至大致都要平衡以及完整,甚至有虚构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是,只要我觉得有意义、有趣的,就把它记录下来,甚至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是我和一般的非虚构写作不太一样的地方。
阿城:我拿到《回望》之后,首先发现这本书有一幅地图,《繁花》也有地图,假如金老师继续写下去,我想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每一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慢慢地,如果这个地图上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的话,上海在时间轴的串联上会非常丰富。我们对这个城市好像对家庭一样开始熟悉了,这是我从金老师的著作里面得到的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企盼金老师的著作把这些点再细致、再深入,像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给出那个时代的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地图。北京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北京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这个地图没有建立起来。
法国有过一个百科全书派,他们对很多事情发生兴趣,对很多的点进行深入的发掘,这个发掘导致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以前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写是被妖魔化的,但发掘下去,发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结构以及原来的环境渐渐地好像一个岛慢慢往上升起来,浮出水面,水流走了,我们看到了遗址,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这个地区清楚了。这个岛对影响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省,这个反省进而导致了对于“革命”的反省,对于革命还是改良这个争论加了新的翔实的资料以供讨论。
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问题:《繁花》的写作很有特点,阿城将金宇澄的这种写法概括为自然主义。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写作,自然主义一直是被贬抑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是什么?
金宇澄:我第一次在阿城这里听到自然主义是非常有用的,我听了之后受益匪浅。包括《繁花》,有人也说要还原到这种地步,是否有意思?我也很犹豫,这样写是不是行?一直在纠结当中。
阿城:说到自然主义,有一些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法国的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中国一直在强调写实主义,什么是写实主义的基础?其实是自然主义。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他们的描写左拉认为没有到底,一定要通过自然主义达到写实的极限。你到了这个极限的时候才能够退回原来的写实主义,把握是不是有分寸、够分量,如果没有这个底线,我们不好把握自己,或者没有对这个底线认识的时候,我们看不清别人的写作或者自己的写作在一个什么样恰当、合适的写实的度。
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现实主义,对于自然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拷问你对现实的认识和你要发扬什么,自然主义不是这样。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写某个细节,写得那么细,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价值观,但是它那么有力量!所以写实主义其实像气球一样飘忽不定,它必然有一股强风来,有一个主流来,随着主流飘。现实主义这个气球要有一根线拴住,这个气球就是你的写作。这个扣在哪儿?自然主义。实际上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金瓶梅》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红楼梦》增加了一点——这是张爱玲对《红楼梦》不是特别满意的原因——它有一个价值观,告诉你该放弃什么,后来贾宝玉还是出家了,很强的价值观使他有这样一个的行为。但是《金瓶梅》不是,你就是看到一个自然的生物体慢慢地没了,本能的东西在里面来回蠕动。中国实际上是有比左拉时间、空间要早的自然主义传统,这个传统被我们伪道德的意识把它的价值否定了,有没有人去接中国自然主义的传统?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没有人敢通篇接上,只是局部接上了。我看《繁花》最兴奋的一点就是它那么多的自然主义性质,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这个“补课”的结果其实是正反应。
我知道自然主义的描写,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本性的你敢直视的。因为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学术上叫做“偷窥”,你敢直视它,实际上就是敢直视自己。你平常没有机会去直视自己,顶多是反悔,我怎么会那么做!当你在自然主义这个底线游走的时候,实际上在看自己、认识自己。